放大资金,增加盈利可能
配资是一种为投资者提供杠杆资金的金融服务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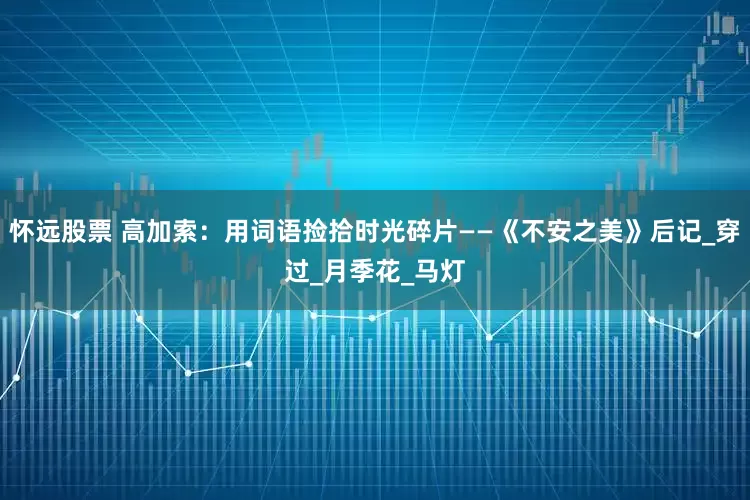
风穿过窗棂时,总带着某种迟疑。像我写下第一行诗的那个黎明,露水在月季花瓣上悬而未落,远处的铁轨泛着冷光,有列火车正碾过晨雾的骨骼。这些年,我总在这样的时刻与词语相遇 ——它们藏在树皮的皱纹里,躲在候鸟迁徙的轨迹中,甚至附着在暴雨冲刷过的街面上,像一群不愿归家的孩子,等着被某个瞬间认领。
里尔克说过:"词语像树,得等到一阵合适的风,才会抖落藏在年轮里的秘密。" 这些年的捡拾,也许就是在等这样的风。
八十年代某个深秋,我在故乡的荒野里遇见一块被雨水泡软的马粪纸。它半陷在泥里,边缘已经发潮发卷,却仍能看出曾经印过的字迹 —— 或许是某个供销社的收据,或许是一封没寄出去的家信。风刮过的时候,它发出细碎的声响,像有人在低声诉说。那天傍晚,我蹲在原地看了很久,直到暮色把纸页染成灰蓝。
——就像诗里那只寻找黑暗的马灯。
初写它时,我正住在济南洪家楼单位的老楼里。楼道里的声控灯总在半夜失灵,每次起夜都要摸黑穿过三级松动的台阶。有天凌晨,我攥着火柴照亮楼梯,火柴微弱的光突然映见窗台上的旧马灯 —— 那是一家建筑公司留下的物件,玻璃罩上布满蛛网,灯芯早已朽成黑灰。可就在那团微弱的光里,我看见灯座上刻着的 "平安" 二字,被岁月磨得只剩浅痕,像两道未愈合的伤口。
展开剩余83%后来我想,建筑工人当年提着这盏马灯走过门前的胶济铁路时,会不会也在某一刻觉得光亮是种负担?就像此刻的我,对着满桌诗稿,突然害怕这些词语太过明亮,会照见那些刻意藏起的秘密 —— 比如文化东路上未说出口的歉意,比如英雄山月季花丛里被暴雨打烂的约定,比如某个冬夜在医院走廊里数过的地砖,每一块都刻着不同的疼痛。
在呼伦贝尔草原,我遇见过一个放牧的老人。他坐在牛群旁抽着旱烟,烟袋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,像坠落在草甸上的星子。我问他每天守着这片空阔,会不会觉得孤单。老人指了指远处的群山,说:"孤单是因为你还没找到愿意听你说话的石头。" 那天傍晚,我躺在蒙古包里听风穿过帐篷的声音,突然想起诗里写过的 "每个怀乡者都握有一条马鞭"—— 原来我们抽打记忆的姿态,和牧民抽打牛羊的姿态,并无二致。
集子里有一首诗写 "黑胶唱片",那是纪念一位故去的友人。他生前总在洪楼西路的旧书摊上淘黑胶,说唱片转动时的杂音,是时间在呼吸。他走的那天,我在他书房发现了一张未拆封的《伦敦德里小调》,封套上有他用铅笔写的批注:"雨大的时候,琴声会发芽。" 后来每次下雨,我都会把唱针放在唱片上,看雨丝斜斜地织进窗玻璃,而旋律里的爱尔兰草原,正慢慢长满济南的青苔。
这些年,我渐渐学会在词语里播种。
在 "八十年代" 里种过羞愧 —— 那年与雨在 1 路公交车上谈论诗歌,车窗映出山大南路图书馆的灯火时,突然觉得所有的高谈阔论都像偷来的麦穗,沉甸甸地压着青春。在 "1987 年的月季" 里种过荒诞 —— 英雄山上手持月季的人们,把花朵当成暗号,却不知道花瓣上的露水,早把所有秘密告诉了泥土。在 "斑马,斑马" 里种过流亡 —— 那些黑白条纹不是装饰,是灵魂在皮肤上刻下的界碑,一半属于故乡,一半属于远方。
最难忘的是写 "车过临淄,想起一位死去的朋友" 时,我正坐在时速 350 公里的高铁上。车窗外的白杨树向后倾倒,像被时光推倒的多米诺骨牌。突然就想起朋友生前说的话:"死亡是生的另一种押韵方式。" 那一刻,所有的比喻都失去了重量,只有铁轨的震动穿过座椅,敲打着胸腔,像有人在远处擂鼓,提醒我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思念,其实都在诗句里长成了森林。
有读者问过,为什么总写 "不安"?
或许是因为见过太多事物的裂痕。在南山的采石场,我看过被炸药劈开的岩石,断面处的结晶在阳光下闪着冷光,像大地裸露的骨头;在意大利北部小镇,我见过被雨水泡胀的报纸,头版新闻上的笑脸正慢慢晕开,变成模糊的光斑;甚至在自家阳台,也见过仙人掌在深夜开花,花苞裂开的声音轻得像叹息,却足以惊醒整个房间的寂静。
这些裂痕里,藏着最真实的呼吸。
二〇〇六年冬天,我在城郊的树林里遇见一只乌鸦 —— 羽毛白得发蓝,正站在光秃秃的槐树上啄食树胶。阳光穿过它的翅膀,落下细碎的光斑,像撒了一地的碎银。后来查资料才知道,这是白化病的乌鸦,因为缺乏黑色素,被同类排斥,只能独自在边缘地带生存。可那天它抬头望向天空的样子,没有丝毫卑微,反而像在审视整个世界的偏见。
写诗的人,大抵都是这样的乌鸦。
我们在人群中保持着奇怪的姿势,既想融入喧嚣,又怕被世俗磨掉羽毛。就像下夜班路上,那个与我并肩走在黑暗的黑衣女子,我们都不说话,却能听见彼此心跳里的平仄 —— 她的银色发卡反光时,像句未完成的诗;我的皮鞋踩过水洼时,像个笨拙的韵脚。有些相遇,本就不需要语言,正如有些疼痛,只能交给分行的文字。博尔赫斯曾说:"诗人是被语言利用的人。" 或许可以更准确地说,我们是被语言选中的守林人,看守着那些无法被言说的沉默。
去年整理旧稿,发现最早的一首写于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。那时,我醉心于诗歌写作,每天夹着诗稿在宿舍和教室、图书馆之间穿行。有天下雨,诗稿被淋湿,字迹晕成一片蓝雾,我却突然在纸页空白处写下:"海浪把盐撒在礁石上,是想腌渍时光吗?" 如今再看这句,依然能闻到当时空气里的青涩,能摸到纸页上未干的水痕 —— 原来所有的词语,都是时光留下的盐粒,在岁月里慢慢发酵出味道。
集子分为三辑,像三个相互嵌套的梦境。
第一辑里的词语,多是在旷野里疯长的野草。它们带着露水的湿气,带着风沙的粗糙,甚至带着某种莽撞 —— 那个 "预感磐石快要来了" 的黑夜, "穿过命运的大雨" 时紧握的伞柄, "在医院" 里数过的点滴……其实都有野草的影子。它们不懂得修饰,只是拼命地从泥土里钻出来,想看看太阳的模样。
第二辑更像一列夜行的火车。车窗外掠过的灯火,是记忆里忽明忽暗的脸 —— 亲人在病床前的剪影,故友在酒桌上泛红的眼眶,陌生人在站台递来的问候。这些影子在诗句里摇晃,像车厢连接处的铁环,碰撞出叮叮当当的声响,那是生活最本真的韵律。
第三辑的句子,都长在深夜的褶皱里。 "与一只英短蓝猫对视" 时的沉默, "在夜色中写作" 时台灯投下的光晕, "扎羊角辫的师妹" 走过操场时扬起的发梢.....它们更安静,也更固执,像冬夜里贴在窗玻璃上的冰花,用最脆弱的姿态,记录着温度的轨迹。
有次在咖啡厅写诗,邻座的人看我反复涂改,笑着说:"年轻人,写完就不要轻易改动了。" 后来我总想起这句话。这些年删删改改,删掉的其实不是词语,是那些过于锋利的棱角 —— 就像把一块石头放进溪流,让时光慢慢磨去尖锐,只留下最温润的轮廓。
所以你会看到,这些诗里没有宏大的叙事,只有些零碎的瞬间:可能是 "宽厚里的星光" 落在咖啡杯里的样子,可能是 "后宰门巷的月亮" 爬过教堂尖顶的弧度,可能是 "乌兰巴托之夜" 马奶酒在喉间燃烧的热度。它们像散落在地上的拼图,单独看时只是块不起眼的彩片,拼起来,才是我这些年走过的路。
去年冬天,我回了趟老家。院子里的老槐树被暴风刮断了枝桠,断口处渗出琥珀色的树胶,像凝固的眼泪。我蹲在树下锯断残枝,木屑纷飞中,忽然想起一位已故诗人说过的话:"树断了不怕,只要根还在,春天就会从裂缝里钻出来。" 那天下午,我坐在树桩上晒太阳,看着树胶在阳光下慢慢变硬,突然明白:所谓写诗,不过是给那些看不见的根须,找到一条呼吸的缝隙。
就像此刻,我坐在书桌前,看窗外的雪落进路灯的光晕里。每片雪花都是一个透明的词语,它们落在屋顶上、树枝上、未寄出的信封上,慢慢堆积成白色的诗行。而那些藏在积雪下的事物 —— 比如月季的球根,比如冬眠的虫豸,比如某个未完成的句子 —— 都在静静等待,等待春天来临时,能从时光的缝隙里,探出嫩绿的脑袋。
我始终相信,所有诗歌的诞生都带着某种地质运动的属性。你看那些嵌在岩壁里的贝壳化石,千万年前它们曾在潮汐里开合,如今却成了石头的心跳。《不安之美》里的句子也大抵如此,它们最初只是些零散的碎屑:晨雾中突然折断的芦苇秆,地铁换乘时陌生人衣领上的霜,凌晨四点晾衣绳上打结的月光......这些碎片在笔记本里沉睡多年,直到某个雪夜,我发现它们正在彼此吸附,像磁石吸附铁屑,渐渐拼出一道发光的裂缝。阿多尼斯说:"诗歌是穿越存在废墟的闪电。" 而这些碎片的聚集,或许就是在等待成为那道闪电。
这些诗,就是我的等待。
诗集定稿那天,我把所有手稿摊在地板上。阳光从窗格漏进来,在纸页上投下长短不一的影子,像一排沉默的刻度。这些诗句诞生于不同的时刻:有的写在摇晃的绿皮火车上,有的写在医院的长椅上,有的写在暴雨倾盆的午夜。它们原本是散落在时间里的星子,如今终于连成了一片微光。
"不安" 从来不是诗歌的敌人。就像钟摆的晃动,正因为有了左右的摇摆,才有了时间的韵律。《钟摆飘荡》那首诗里,"一个早起的人开始出发 / 准确到以分秒计 / 在钟摆的飘荡中 / 穷人赶路,富人慵懒 / 中产阶级探讨意义",说的正是这种永恒的时差。诗歌捕捉的,恰是这种追赶过程中的喘息与回望,是在奔跑时不忘捡拾路边的野花。
我愿意把这些诗歌献给所有在黑暗中仍举着灯火的人,献给所有在窒息中仍努力呼吸的灵魂。如果某个瞬间,你在这些句子里读到了自己的影子,那一定是风把我们的回声,吹到了同一个角落。
毕竟,万物都在寻找自己的共鸣。就像那盏马灯,终会在最深的黑暗里,遇见懂得它的眼睛。
发布于:山东省十大配资平台app下载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